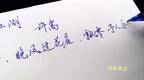温铁军的“三农”往事:世纪困境应做何解?
2018-09-16 23:01:18
来源:
凤凰网财经
作者:
郑雨婷
每每提到“中央一号文件”,“三农”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凤凰网财经郑雨婷)每每提到“中央一号文件”,“三农”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在每年下发的第一号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40年里,有20个“一号文件”都在聚焦“三农”问题。
而谈到“三农”问题,温铁军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相比其他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数人一听到这个名字时都会有点踌躇——他是谁?确实,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然而在和记者聊到农村问题时,这位年过六旬的学者脸上还是焕发出了与年龄不相符合的神采。
8月初的北京气温接近40度,记者在人大咖啡厅见到温铁军时正值午后,在这个一天中最炎热最令人觉得困乏的时段里,温铁军却没有展露出丝毫倦意。高大、温和、没有架子,这是记者对这位“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的全部印象。
两个“十一年”
1951年,温铁军出生在北京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当时他初中还没毕业,“文革”大潮就席卷了全国;17岁的温铁军也没有逃脱这场政治运动的影响——那年,他被派到山西汾阳插队,“每天能在火车站扛大包”成了少年温铁军最大的梦想。
之后的十一年里温铁军并没有闲着,有一年回家探亲的时候碰到了小时候一起玩的“孩子头”,“咱们一块儿当兵去,你去不去?”听闻邀请,温铁军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就这样去了,完全没有什么自己的选择,当兵之后,也无非是做个好战士,反正就是一个认真做事、老老实实听话的人。”当完兵,“闲不住”的温铁军又接着当了三年工人。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经历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他学会了从农民和基层的角度思考问题,开始关注农民、农村的发展。“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懂得了工人。”温铁军感慨道。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新闻的他最终却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十一年的工农兵经历让温铁军的这段人生轨迹变得顺理成章。
也许是受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毕业后不久,他就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骑着摩托车沿黄河考察了8省40多个市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失联”了将近4个月。“回想起来,很多情境是在历险。比如在沙漠里边,摩托车是开不动的,只能推。我的同伴都比我年轻,但都走不动了,趴在沙子上一动不动。我骂他们、打他们、踢他们,硬逼着他们往前走。好玄在天黑之前走出了沙漠。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他们说:‘老温哪,多亏了你!要不,哥几个得死在沙漠里边。’”多年后温铁军在向媒体谈起这段往事时,仍然记得里面许多险象环生的情节。
这一年是1985年,也是温铁军的转折之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民生经济初露锋芒,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资本投入加大,社会迎来了一波肉眼可见的“高增长”。彼时的农村并非只有一望无际的农田,小型的农产品加工厂和设备制造厂也在繁荣生长,农民摇身一变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小型经济从业者。“八十年代的内需拉动,除了当时的做多政策体系之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温铁军总结道。
1985年,温铁军迈进了“九号院”的大门。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当时号称中国农村研究的“黄埔军校”——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办公所在地;在这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很多都已成为活跃在政坛、学界和商界的翘楚。
比温铁军早3年来到这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如今回忆起西黄城根南街的这个办公室也感触颇深:“在几乎整个80年代,九号院是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中枢之地,可谓‘极一时之盛’。第一批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在这里酝酿形成。”
同样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姚监复在多年后向媒体回忆说:“(我们)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搞调研,三分之一的时间汇总、统计、讨论,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起草文件。”
而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温铁军,在刚进政策研究室的时候还只是负责编辑内刊的工作;但是他一边编内刊,一边学习各种农村知识,也逐渐开始了农村调研的道路。这段工作经历可以说是温铁军人生中弥足珍贵的一部分,他也一直将它视为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只是个调研员而已,了解了一些基层的情况。”
那几年,温铁军也在慢慢把目光延伸到中国以外的更广袤的世界。得益于扎实的英语功底,温铁军在1987年被公派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和世界银行进修,并获得了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有媒体撰文称:“温铁军读新闻系,参加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和培训,学会的是用是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不得不说,这确实给温铁军的知识结构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当时)送我出去学的是‘方法’而不是‘理论’,这个‘方法’是必须跟世界银行利用(它的)全套制度来改造中国的项目进行某种对接。”温铁军向记者坦言;当时,世界银行正好给中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政策性贷款,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体工作就是建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
“我是里边儿做技术活的,我在做试验区的检测和评估。”温铁军说道,“用数据体系的建立和分析来应对世行对中国制度问题的挑战,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用西方的话语,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话语来做同样的诠释。”这一做就是很多年——从1987到1998年,温铁军先后担任检测处副处长、调研处长、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我一直干这活儿,所以我现在能够用中国自己的发展体系,有数据支持的这种体系和西方进行对话。”
很显然,这个“十一年”,温铁军还是没有闲着。
1990年以后,中国迈入了工业化高速成长的时期,“三农”领域的矛盾也逐渐成为显学,按温铁军的话说,“90年代的中国是农民发生群体事件最多的年代,也是农民负担最重的年代,也是农业形势最严峻的年代”;经济的高增长与农业三要素对非农部门的关系直接相关,导致了农村土地的大量征占和劳动力不断流出,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内需长期不振等问题日益严峻,农村改革开始陷入僵局。
“90年代给农村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工业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工农收入差距必然扩大,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如果你要扭转规律,就好比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是人地资源比例的矛盾……”姚监复说道;在他的印象里,这段时间的温铁军仍然在试验区埋头工作,很少对外发言。
但温铁军还是“搞事儿”了。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温铁军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Next China(下一个就是中国)!”这是当时温铁军在纽约街头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他自己反倒不信这个邪,“但是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没门儿,我只是相信中国会稳定发展。”于是凭着这股执念,温铁军毅然背起包裹,只身一人前往苏联考察,还差点受到处分。
“到了那儿,我下了火车,找个当地的小咖啡馆,就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然后就住在那儿跟当地的老百姓谈。我采用的是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我要接触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看一点什么材料,吃别人嚼过的馍对我来说是吃不出味儿来的。”话里行间不难觉察出,这段“说走就走”的往事对温铁军的意义确实非比寻常,“我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是住在一个战争难民的家里,楼下的客厅沙发上住着一个怀孕的妇女,是被打出来的。除了找老百姓以外,我也找了私有化部,找那些制定私有化的大学者谈,他们也接待我,因为我拿着我导师写的推荐函,说我在做有关的研究。”
七个苏东国家温铁军都走了过来,当时正是战火纷飞,从意大利出发的时候当地人问他:“那里正在打仗,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要看到这个情况,”温铁军的态度很坚定:“我走了40天,被打晕过,也被偷过。亲眼看到了混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所以现在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因为我亲眼看到过激进给老百姓带来的代价。这些全部是我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经验,当你走进去亲眼看到那一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什么是转型代价,那是老百姓的苦难。”
这一圈走下来,温铁军发现,苏联解体其实是因为国家一直停留在实体经济阶段,推行的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换货贸易体制。“你给我多少吨小麦,我给你多少台机床;你给我多少台汽车,我给你多少艘船。”换货贸易用国际价格的三分之一来计价,于是它的总量就是国际西方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没有进入货币经济。
接受教训后,1992年中国告别了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彻底改用货币作为商品交易的中介;同期,国内开始增发货币,开始了逆周期调节,赶出了西方封锁。同年,中国开放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进行房地产改革。
1994年,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降57%,大贬值刺激了出口。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改变:苏联解体后,美国带着对全球的统治力,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纳入世贸组织,一并纳入的还有农业和金融的自由贸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农业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开放问题,还涉及到农业政策、农产品出口竞争、出口补贴、有关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和深层次的管理等方面的挑战。于是到了后来,农村乡镇企业因为没有优惠全都垮掉了,整个中农工建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40%以上。
农业发展的滞缓被温铁军看在眼里。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这也被认为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关键文章。
世纪困境作何解?
1982到1986年,中央曾连续下发5个与农业有关的“1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此后便中断了18年;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才又开始重新聚焦“三农”。
温铁军却从未间断过。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在呼吁“三农”问题:“不能只强调农业政策,不讲农村,更不讲农民。眼中有数,心中无人,咋行!”那个时候,温铁军就在根据农村试验区研究成果写书、读学位、研究近代经济史,一刻也没有闲着。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反思资本深化所造成的“三农”困局。
1997年,粮食大量积压,13年前增产不增收的“卖粮难”问题再度出现,由此导致的农民收入连续下降,使“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温铁军在当时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于是,人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第一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3年是“三农”问题突然变得尖锐的时期,农民负担过重作为“三农”问题的表象渐渐浮出社会生活的水面。在林毅夫看来,“三农”问题在当时之所以变得严峻,是因为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小,新增就业机会少,造成了应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又返回乡村;此外,众多乡镇企业也在竞争中纷纷倒闭,一方面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另一方面也迫使早先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又回流到农业,如此背景之下,农民收入增长愈加缓慢,“三农”问题雪上加霜。
彼时温铁军所做的《世纪末的反思》一文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他也会时不时“口出狂言”:“如果把现代化当作终极目标,把发展主义当作达成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会得出‘农村农业必然衰败’的结论。”
这一论调在当时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背景下无疑受到了外界各种解读。
“首先你需要给我一个没有充满那么多‘罪恶’的现代化,你要给我一个有成功经验可循的发展主义的样本,我们才可以讨论问题。”温铁军向记者说道,“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化经验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前史是殖民史,而殖民化的大规模掠夺是反人类的,最终殖民化的代表无外乎就是所谓的奴隶制三角贸易。”
“在中国,‘现代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一种‘激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别激进’,不是‘反’现代化,而是‘解构’现代化。”在温铁军眼里,激进地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可能导致农村社会与城市之间更加难以平衡,现代化成本过高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如果你不去解构它,你怎么能够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
那么我们又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呢?“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城市现有的这一套现代经济制度,对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农村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温铁军直言。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自己也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翟城往事与温铁军的“诺亚方舟”
在了解温铁军之前,很少有人知道翟城在哪里。
十多年前,一个乡村建设学院的落地令这座位于河北定州市一隅的小村庄与温铁军的人生轨迹交叠在了一起。
然而对翟城村民来说,“乡村建设”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因较早推行村民自治,翟城村在民国初年就被定为模范村;1926年的时候,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更是在这里推广平民教育运动,说它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一点也不为过。
2003年7月,温铁军与几家单位合作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乡建学院的出现被视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派”领袖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延续。
沉寂多年的翟城,再次蜚声全国。
据原翟城村支书米金水回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其实“出于偶然”;“2001年,南方一位专家来村里,提出一定要打好‘晏阳初’这个品牌,以后的农产品就可以用‘晏阳初’商标。”

2003年7月挂牌成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资料图)
2002年,温铁军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平台,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民间浪潮席卷全国。03年春节,《中国改革•农村版》编辑邱建生带队到翟城过年,住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米金水去探望时看到邱建生写了一副春联:“念先辈平民教育诚可嘉,看今朝乡村教育慨而慷。”
这副对联立刻引起了米金水的注意,“我一看,原来他们也对晏阳初感兴趣,我就觉得村子的机会来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之后他们还专门找到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讨论了建学院的想法。2003年7月19日,翟城村花了39万元买下村西一处废弃的中学作为乡建学院的校址;多年后米金水向媒体谈起这件事时,脸上还带着些许自豪的神色:“我在喇叭上一说这个想法,仅仅两个小时村里就筹足了30万。”
起初,温铁军并没有答应邱建生办学院的事;邱建生提了3次,他才点了头。
学院落脚以后,翟城村民们的生活顿时热闹了不少,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和读书小组等组织,村民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此外,温铁军还请来了海外著名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他的妻子还认养了一头小毛驴,并给它取名“教授”——当时,温铁军刚到人民大学当教授。
有人说,当时的翟城不同于晏阳初时期的翟城,很多时候更像是温铁军倾力打造的一艘“诺亚方舟”。然而这艘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方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要饱享各种关爱与赞扬,也要承担外界的审视和质疑。
最直接的质疑就来自村里。
晏阳初学院成立之初,翟城的许多村民以为办学校了,再过不久村西边就会有大片高楼林立,各地学生在此云集。“当初我们以为,最低他们也要引进点外资或者办个厂子什么的吧…..”一位村民向媒体回忆道。
时间久了,村民们开始觉得知识分子们的很多试验太过理想化了。夏天,杂草在试验田的路边疯长,温铁军坚持“生物防治”,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杀虫;学院在试验地里种的西瓜,被描述成“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学院建的生态厕所、“地球一号”生态建筑等被村民笑称为“土屋”。
“村民对学院的不认可,主要原因是学院没有给村民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利益;学院并没有给村里‘办厂子’‘跑项目’‘引外资’,村子的经济发展状况没有明显改观,村民也没有得到多少眼前的实惠。”一位研究人员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在翟城,知识分子求解乡村问题的探索已经承续了近百年;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更加宏观的中国农村时也不难发现,政策往往比理念或模式更能产生现实效用。
这恰恰就是温铁军等人与翟城村民之间的矛盾所在——能源危机、人多地少、美国模式……这些话题在村民们听来总觉得离现实生活有点遥远,即使后来学院帮助村里组建的合作社让村民们真正得到了实惠,但由于统购统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短时间无法纡解,社员之间也一度出现信任危机。
谈及翟城合作社的坎坷,温铁军曾经向媒体表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能指望合作社一年多的发展就把问题解决了,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翟城合作社也不例外。”
2003年7月19日到2007年4月12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翟城存活了3年零9个月。

晏阳初的半身像仍立在学院的大门口,墙体上的标语显示着当时筹建的雄心(资料图)
“我尽量笑着说,”多年后再提起这件事,温铁军的话里行间还是透着藏不住的遗憾,“这个事儿我得道歉,我们确实造成了麻烦。”但遗憾之外还是有值得欣慰的成果,“三年下来,我们已经完全在这块40亩的土地上彻底恢复了有机生产,完全形成了一套六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温铁军说罢,脸上的笑也明朗起来。
三年下来,无论是“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还是农村合作社的运行,晏阳初学院一直活跃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温铁军也数不清有多少次站在学院的一角或是田间地头接受采访。虽然结局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后来温铁军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多少也与这些乡村建设的经历分不开。
“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农民的代言人。” 2003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出这番话时,站在一旁的温铁军显得有些腼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遗憾还是遗憾的,但我仍然愿意微笑着解释这个过程,”温铁军向记者坦言,“我们有我们客观上造成的压力,这个我们理解。现在河北当地的一些请你拿知识分子在跟地方商议要重新恢复(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们也乐见其成。我不属于那种‘你必须得给我承认错误,我要去诉讼,我要求赔偿’(的人)。”温铁军说这段话的时候始终平和地笑着。
笑眯眯地揭短;笑眯眯地讲他一手创办的乡建学院被取缔;笑眯眯地谈及理论界“内生的反智”……“笑眯眯的”,这是大多数见过温铁军的记者对他的一致评价,然而平和的性子背后,那股年轻时候较真的劲儿却一直都在。
毕竟自始至终,背着背包穿越苏东战火的人是他;田间地头谈笑风生的人,也是他。

为您推荐
热门文章
-
华为发布一重磅芯片!全新供应商名单曝光
-

暴涨1700%,“血洗”华尔街!美国散户史诗级抱团,“干翻”对冲基金
-

“妖股”暴涨300%!美国散户抱团打爆华尔街空头,白宫监管急发声
-

“敦煌毁林案”:13300亩还是6000亩?有图有真相!
-

原董事长被查、两名前高管被立案!62年老牌企业怎么了?还有多少雷?
-

突发退市警讯!曾与中兴、华为并列,这家昔日的电信巨头能否断臂逃生?
-

澳方希望中方取消对其煤炭进口的禁令,商务部回应
-

55万股民“哭了”!又一批爆雷股:巨亏超100亿!更有强平、退市在即
-

“雷声”不断!一晚21家公司齐发预亏公告,累计亏掉104亿!(名单)
-

燕郊有业主房子免费送,需承担房屋转让费用,还有剩下的贷款
-

新华财经调查|“一瓶难求”的茅台:谁在炒、谁在喝?价格刹得住吗?
-

巨雷接连炸响,这家公司暴亏近25亿!投资者:气得手都在抖!
泡泡直播
精彩视频
-

当西安鼓乐邂逅圣彼得堡 俄女大学生惊艳展示“中国古风”
-

拜登签行政令:打击“歧视亚裔”仇外心态
-

萌娃得知不用洗头内心狂喜:捂嘴笑“憋出内伤”
-

佩洛西强势发声:敌人在众议院内部 有议员带枪来上班!
-

男子网恋4年送出200万元,期间女友9位亲人去世,真相让人无语
-

蓬佩奥又来抹黑新疆?这位“00后”哈密小伙有话说
-

89岁老人被送去火化 进焚化炉一刻发现还活着
-

男子小区内遭捆绑殴打后死亡,姐姐:小区里多次发生业主被打事件
-

高速上倒车为捡猪 货车司机被扣12分
-

美国真实意图是解体中国?崔天凯挑明美方危险做法 铿锵发声
-

男子骑车摔倒后立马后退 几秒后火车开来把摩托碾得粉碎
-

白宫前顾问发女儿半裸照引争议 警方介入调查

凤凰财经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