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的中国图谋 中国距离世界有多远?(2)
数十年来,达沃斯上的“中国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早期的政治力量为主,到后来的企业家力量的加入。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早在1992年就参加达沃斯论坛,见证了这种变化。在他看来,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达沃斯请李鹏总理去,是有一定胆量和压力的,当时的论调是中国要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达沃斯论坛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说,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坚定决心。1998年是另外一个转折点,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充满了疑问,李岚清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作了《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讲话。“1992年、1998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甚至对国外的大规模投资起了决定性作用。”吴建民说。
在芮成钢看来,达沃斯最显著的变化是“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中国威胁论,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坏得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中国的地位和声音我觉得还是不够。”2007年3月10日,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达沃斯归来分享沙龙上,前UT斯达康中国总裁吴鹰如此表示。让吴鹰印象深刻的是一件事件,在一次电信行业会议的上,有十几个电信行业的领军人物参加,其中也有中移动总裁王建宙,“王建宙来晚了,我特地跟身为主持人的摩托罗拉总裁爱德华·詹德说:中国移动的老板来了。但他并不重视。”
并非去过达沃斯的每个人都在达沃斯感受到了兴奋。正略均策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赵民表示,他去过达沃斯四五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没什么意思,贫困、环保、全球变暖,第一次听觉得挺有意思,第二次还能接受,第三次听完以后就觉得烦了。”在他看来,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关心的还是企业的发展、运营等实际问题,更虚、更空、更高的问题,没有办法在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心中引发共鸣。
“英语短板”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反复被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副总监张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央电视台英语主播芮成钢、原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潘承烈提及。“在达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讨论的形式进行,不仅仅要会英语,还要能够用英语探讨行业、专业问题。这成了多数中国企业家迈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这对同样是新兴市场热点国家的印度为何在达沃斯表现活跃给出了理由。英语基础好、民族性格开放让印度企业家在达沃斯大大抢了中国的风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英语是中国企业家在达沃斯群体失语的重要原因。在田溯宁看来,中国企业家与达沃斯之间的主要障碍是畏惧心理。“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主人。别人不理你,你就主动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达沃斯,中国力量一直是缺乏组织。印度在达沃斯组织了“印度之夜”,耗资300万美元,邀请达沃斯与会者一起狂欢,将印度推销给世界。这让不少中国企业家感觉很受刺激,甚至有中国企业家提议在达沃斯举办“中国之夜”。而连续7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芮成钢建议:“中国企业家一定要带着问题和具体的目标去达沃斯,否则可能就只是看了个热闹。”
达沃斯运作之谜
每年夏天,大马哈鱼都会排除万难,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时候,有一群全球顶尖人士都要经过10-20个小时不等的舟船颠簸,辗转到瑞士一个雪山下的小镇,住在拥挤窄小的房间里面,度过充满高密度谈话、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
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又一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
“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让欧洲和英美企业家聚在一起,有一个交流的机会。随着论坛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认为,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的进步,必须要靠企业和政府联合起来,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挑战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位世界经济论坛员工告诉记者,在达沃斯内部,大家把施瓦布视作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相比,世界经济论坛的最大区别是非盈利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中国负责人于江向记者强调,“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蒋睿杰(Jeremy Jurgens)称,论坛会从三个方面给CEO会员带来启发:首先是宏观趋势与形势的判断;其次是商业层次上的交流;第三给CEO们提供商业之外的灵感启发,比如,论坛会请天文学家、艺术家等跟CEO们进行头脑风暴。
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万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国汇市收盘价),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300多名,来自五十多个国家。
有人评价,达沃斯论坛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对于达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过“非盈利但是很赚钱”的评论。赵民则认为,“虽然世界经济论坛不盈利,但是与其相关的媒体、投资机构都非常赚钱。”
达沃斯在规模和规格上能够远远超越其他国际经济论坛,除了非盈利带来的“公正”效应,时间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芮成钢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个高端经济论坛就够了,谁最先做出来,就最有竞争力。”
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他们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快乐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
“我们是在运营一个社区。”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响力的社区。围绕这一社区,有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区域合作伙伴、会议合作伙伴等,分别提供场地、车辆、餐饮、电子设备等的赞助,和一般的商业赞助不同,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现在论坛上。于江认为,“这就是社区的精神,把论坛当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无偿的。如若不然,大企业和小企业永远无法平等对话了。”
在大众层面,《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的品牌影响要远远超过达沃斯,但这并不会让世界经济论坛有任何不安。“我们目标客户很明确,就是政府部级以上领导和大型企业的CEO和董事长。我们只在精英层面上推广,大众层面的主动推广根本没有,也没有用,做了或许反而会损害品牌。”
在议题设置上,达沃斯年会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政治和商业各占50%。达沃斯论坛的员工会不定期的到会员企业去,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另外,论坛会通过世界各地的专家沟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运用到商业领域会带来哪些变革。
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金融时报》则有专栏文章对达沃斯批评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讨论常常退化成为陈词滥调。坐在大厅后面花上几个小时听人们讲‘经营全球风险的有效领导’——本年度达沃斯主题之一——你会睡着的。”
在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看来,达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该机构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政府、经济和舆论界开展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该机构又充当了一个传教士,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规则通过更委婉的渠道灌输给其它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乃至认同、膜拜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而这些规则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论坛主席施瓦布是达沃斯论坛的真正推手,绝大多数与施瓦布有过接触的人都把他称作“有远见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现出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大西洋(17.88,-0.12,-0.67%)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如是说,达沃斯的战略重点也开始转移。
中国正成为施瓦布的未来重点,对于达沃斯的中国图谋,梅新育直言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达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除了传统的权力中心之外,还必须在崛起中的权力中心加强影响力;否则,随着老权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额下降,仅仅在老权力中心拥有影响的社会机构影响力也就将随风而逝了。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崛起中的权力中心。”
重启中国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之路并不顺利。
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国众多人口形成的广阔市场。”曾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到这一点还是满怀敬佩。“讨论会能够迅速成型,国家经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协调作用。袁宝华当时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所以最后确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来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负责与达沃斯方面的合作超过10年。
在“中国企业高峰会”创立之初,双方合作相当愉快。通过国家经委,每次峰会中国企联都能够保证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和“部长级报告”,中外企业家可以在部长报告之后直接面对面向部长提问。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给对于政策难以把握的中外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借助自己在发达国家的号召力,将外企引入中国。据介绍,西门子、大众第一次进入中国,都是通过“中国企业高峰会”这一渠道。
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强化,“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联的合作也摩擦频繁。“最开始,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换过几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态度越来越倨傲。”潘承烈告诉记者,双方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也产生了分歧。以前双方的财务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请中外企业,在国外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中,前50家注册费由中外双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获得15%;国内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则全部由中方享有;论坛开支由外方负责。后来,外方不再把海外企业参会费用与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担论坛开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见到中国大使吴建民时,提出“中国企业高峰会”能否更换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议被拒绝后,“中国企业高峰会”虽然仍旧每年照常举办,但是已经乏人经营、日趋没落。
现在,当达沃斯要重新启动中国,反思“中国企业高峰会”的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总在一个城市举办,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经理马德志这样总结。这一点,潘承烈也有共鸣,“每年都开同样的会,不可能部长每年都来,后来可能就是副部长或者其他官员了。”这正是夏季达沃斯在确定首届论坛选择大连之后,马上公布下一届将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经济论坛筹措夏季达沃斯时,没有继续选择中国企联,而是选择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夏季达沃斯的筹备中,国家发改委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已经显现无疑。“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注册的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尚未有这种性质的组织,注册成立办公室非常麻烦。发改委出面协调民政部、外交部,为论坛单独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团组织的类别,方便我们注册。”张励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从达沃斯决定在中国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类似的国际机构在北京成立代表处的平均时间大约是3-4年。
2005年1月,中国常务副总理黄菊带团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举办全球新领军者年会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对中国企业有很大帮助”的反馈。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进攻”。在2006年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副总理曾培炎与施瓦布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夏季达沃斯”。同年9月,参考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做法,通过投标的方式,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了大连作为举办城市。
“世界经济论坛将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冬季达沃斯,一个是夏季达沃斯。”施瓦布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上如此表示,显示出对夏季达沃斯的看重和倚赖。冬季达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强,全球新领军者年会则定位于新兴市场500强,商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比率则调整为7:3。
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年营业额达到1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长,都在被邀请之列。预计参会的500家企业中,会有1/10来自中国。于江表示,“年营业额超过45亿美元的,我们会直接邀请它参加冬季达沃斯。希望现在参加夏季达沃斯的新兴企业,可以很快毕业,加入冬季达沃斯的俱乐部。”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个《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注册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想了解中国,更想见见新兴企业和挑战者。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竞争对手。”
但是,达沃斯论坛始终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本土化难题。据潘承烈回忆,达沃斯派到中方的代表,虽然看似越来越多的华裔,但是对中国的了解却越来越少。达沃斯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达沃斯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后来在北京建立办公室。
更大的难题是议题设置。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话题在达沃斯上炙手可热,但是,不少中国参会者都感觉讨论相当初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达沃斯对中国虽然足够关注,但是理解未见得足够深入。
“作为一个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达沃斯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达沃斯是一个外国机构,对中国的了解很浅,“外国人、华裔和非常少数的中国人,都非常年轻,你说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
“达沃斯最无聊之处就在于谈中国。去的中国人太少了,嘉宾凑不够,就邀请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讨论中国话题,或者是请一个中国管理咨询专家评论中国环保问题,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赵民直言,“总有人说中国人在达沃斯是过不了语言关,这很可笑。谁规定中国移动的老总必须要说英语,行业讨论配一个同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反而被放大了。”
达沃斯的闭门行业会议,往往都是邀请行业前20-30位的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即便入围也数量有限,性格内敛的中国人如果感觉势单力薄就发言很少,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这种负面的评价已经反馈给达沃斯,张励告诉记者,夏季达沃斯最重头的工作,即是如何让中国企业家更有效的参与到论坛中,这些会通过一些细节性的安排来保障。“重点不是把中国企业会员数量增多,而是怎么让现有的会员更有效的利用这个平台。”
张励认为,夏季达沃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会议太多了,竞争激烈。“要不断地解释: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不能有长时间的演讲?参会能够得到什么?”
达沃斯的三大价值观“平等、非正式、发人深思”,看似简单,要照搬到中国来并不容易。在达沃斯,国家元首带随从最多不过10多个人,世界首富经常单身前往。这让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一些官员和企业很不适应。达沃斯需要在保证论坛品质和风格的前提下,尽量把中国因素都容纳进来。“一个大的冲突是,达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对话,但是有些领导更喜欢大段时间的发言。于江告诉记者,“要把冬季达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贝到中国来很难,可能需要几届的调整。”
在形式上,达沃斯能否复制到大连也面临考验。“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个小时聊天的,中国没这个习惯。”马云笑说,“达沃斯的商业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达沃斯必须以亚洲为中心,必须以中国为中心。” 来源:《中国企业家》
相关专题: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
作者:
李浩翔
编辑:
xuz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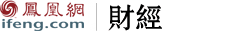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